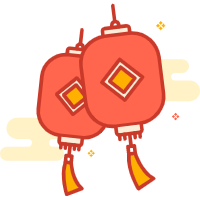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两大预言
乔治·奥威尔的《1984》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Brave New World》
-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而是人们自己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而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读书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而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担心,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一种伟大的媒介-隐喻 (media-metaphor) 转变正在美国发生。这种转变导致了我们许多公共话语的内容变成了危险的无稽之谈。让我们跟着作者的阐述来看看谁的预言可能性更高
核心概念
“媒介即隐喻” (The Medium Is the Metaphor)
这与马歇尔·麦克卢汉 的“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说法相似,作者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媒介的形式与其说是具体的“讯息”(message),不如说是**“隐喻”(metaphor)**。
媒介的形式(包括其允许的符号形式)不会对世界做出具体的、具体的陈述,而是通过不引人注意但强大的暗示 来强制推行其对现实的特殊定义。
我们的媒介-隐喻为我们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世界,并为世界是什么样子提出论证。
理解媒介的隐喻功能需要考虑其信息的符号形式、信息来源、信息数量和速度,以及体验信息的语境 (context)。
“媒介即认识论” (Media as Epistemology)
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本质和范围的学问,文中代指文化如何定义知识、真理以及智慧。
新的主要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媒介通过鼓励某些智力运用、偏爱某些对智能和智慧的定义以及要求某种内容来实现这一点。简单地说,媒介通过创造新的“讲真话”的形式来改变认识论。
作者认为,电视创造的认识论不仅不如印刷品基础的认识论,而且危险而荒谬。
符号环境的变化就像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起初是渐进和累积的,然后突然达到临界质量。电子媒介已经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符号环境的特征。
“会话” (Conversation) 的概念
作者将“会话”视为一种隐喻,指代所有允许特定文化人群交换信息的技术和手段。所有文化都是一种会话,或更准确地说,是多种符号模式进行的会话的集合。
公共话语的形式调节甚至决定了这些形式能够产生的内容。
简单的技术会限制内容的复杂性。例如,狼烟(smoke signals)这种原始技术不足以表达复杂的哲学论证。“当日新闻” 这种内容形式在没有相应媒介(如电报及其后续媒介)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电报使得去语境化的信息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跨越广阔的空间传播。当日新闻是我们的技术想象的产物,是一个媒介事件。
印刷术文化
印刷术作为一种媒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公共话语形式。在印刷术主导的文化中,美国的话语通常是连贯、严肃和理性的,公共话语倾向于以事实和思想的连贯、有序的排列为特征。
这种话语所针对的公众通常有能力理解和处理这种话语。在印刷文化中,作者会努力避免说谎,避免建立自相矛盾、没有强有力支撑的、不合逻辑的联系。因为读者会很容易注意到这些错误。
印刷术促进了分析性思维。矛盾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是衡量真理或优劣的标准,脱离语境会使意义扭曲,而连续、连贯的语境是感知矛盾的基础。印刷术虽然促进了现代个性观念,但也破坏了中世纪的社群感。它创造了散文,但使诗歌成为一种奇异和精英的形式。它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但将宗教情感转变为单纯的迷信。它帮助民族国家成长,但也使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肮脏甚至致命的情感。印刷术作为隐喻和认识论,创造了一种严肃且理性的公共对话。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乐观地表达了印刷术的含义:如果所有人都学会阅读,所有观点都可以通过文字传播,并通过投票选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那么一切都将获得成功。
即使在商业领域,理性的、印刷术的话语的回响也随处可见。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广告商认为他们的顾客是有文化、理性、善于分析的。美国报纸广告的历史本身可以看作是印刷术思维下降的隐喻。它始于理性,终于娱乐。
电子媒介的兴起与文化转变
电报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信息的含义,将其作为一种商品。而几乎同时,摄影术的发明者路易斯·达盖尔 (Louis Daguerre) 也在重新定义自然的含义,甚至可以说是现实本身的含义。电报创造了一个由陌生人和毫无意义的数量组成的邻里;一个片段和不连续性的世界。它使得去语境化的信息得以快速传播。
摄影术,虽然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但它实际上与语言不在同一个话语世界。将摄影称为“语言”是一种危险的隐喻,因为它模糊了两种交流模式的根本差异。摄影术是一种只讲述特定性的语言,摄影只“说”具体事物,其图像词汇仅限于具体表征。它无法处理看不见的、遥远的、内在的、抽象的事物,只能拍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一个片段。抽象概念如“真理”、“荣誉”、“爱”无法通过图像词汇来谈论。照片将世界呈现为对象,语言则呈现为思想。照片缺乏语法,无法与世界争辩。它呈现出世界为客体 (object),而非思想 (idea)。它是一个事实 (fact) 的世界,而非关于事实的争论或从中得出结论的世界。
照片暗示如果我们接受相机记录的世界,我们就了解了世界,照片的认识论偏见暗示如果我们接受相机记录的世界,我们就了解了世界。但所有理解都始于我们不接受世界表面的样子,这需要语言来挑战、争议和审问,语言是挑战、争辩和审视表象世界的媒介,词语“真”和“假”来自于语言的世界。一张照片本身不提出可辩驳的主张或明确的评论,因此它不可反驳。照片与语言记录经验的方式不同。语言需要在命题序列中才有意义,脱离语境会扭曲意义。但照片没有“脱离语境”一说,因为照片不需要语境。摄影的意义在于将图像从语境中分离出来。
摄影术将世界重塑为一系列独特的事件。在一个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中间或结束。世界是原子化的,只有当下,并且不需要是任何可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
电报和摄影术将新闻从功能性信息 转变为去语境化的事实。这导致人们发明了伪语境,以便将原本无用的信息付诸某种看似有用的用途。填字游戏、鸡尾酒会、电视游戏节目都是伪语境的例子。
进入电子对话的其他媒介,如电影和广播,都遵循了电报和摄影术的路线,放大了它们的偏见。
这些电子技术共同创造了一个“躲猫猫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事件或那个事件突然出现片刻,然后又消失。这是一个缺乏连贯性或意义的世界。
电视将电报和摄影术的认识论偏见发挥到了极致,将图像和即时性的互动提升到了一个精致而危险的完美程度。它将这种偏见带入了家中。
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几乎所有公共利益的主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都通过电视呈现。
电视文化的影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进入电子对话的媒介(如电影、广播、电视)遵循电报和摄影的脚步,放大了它们的偏见。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躲猫猫世界”,事件瞬间出现又消失,缺乏连贯性和意义,不要求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但极具娱乐性。电视将电报和摄影的认识论偏见发挥到极致,将图像和即时性提升到了一个精致而危险的完美境界。它成为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
作者用受污染的河流来比喻我们的符号环境。电子媒介已经污染了公共传播及其周边景观。虽然印刷品和阅读仍然存在,但其作用已不再相同,印刷认识论已成为残留的认识论。
电视引入了一个新的语法部分:“现在……接着说”:这个短语不连接任何事物,而是将一切事物分开。它是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常用,表示刚刚听到或看到的内容与接下来要听到或看到的内容无关。它承认了由加速的电子媒介描绘的世界没有秩序或意义,不应被认真对待。
在“现在……接着说”的世界里,不连续性是基本假设。在不连续的世界里,矛盾作为判断真假或价值的标准是无用的,因为矛盾不存在。
电视最强的优点在于它将个性带入我们的内心,而非将抽象概念带入我们的头脑。例如,“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节目中,克朗凯特比银河系更受欢迎。吉米·斯瓦加特 (Jimmy Swaggart) 比上帝更受欢迎。这使得布道者成为名人,宗教成为表演,甚至被作者称为亵渎。
电视使得我们进入一个连续的、不连贯的当下。历史变得无关紧要。
有人认为电视是新的国家宗教。它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普遍的课程,并通过一种隐藏的税收形式资助,无论你是否观看。解放不能通过关掉电视来实现,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它。
媒介与技术的区别
为了理解电视的影响,需要区分技术和媒介。技术就像大脑,是一个物理设备。媒介就像思想,是将物理设备投入使用的结果。一个技术通过采用特定的符号编码,进入特定的社会环境,并渗透到经济和政治语境中,从而成为媒介。简单来说,技术是机器,而媒介是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智力环境。每种技术都具有内在的偏向,预设了某些使用方式而非其他。
警告
回到开头,文化精神衰退有两种方式:
- 奥威尔式:文化成为监狱。通过思想控制、严密监视等手段。
- 赫胥黎式:文化成为滑稽戏。人们不是被剥夺信息,而是被过量的信息所淹没,这些信息无关紧要且不连贯。
作者认为,我们的世界更接近赫胥黎的预言。
- 赫胥黎相信教育与灾难赛跑。他强调理解媒介的政治和认识论的必要性。
-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的问题不是人们在笑而非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止了思考。这指的是缺乏对媒介影响的深刻意识。
如何应对?
- 唯一有希望获得对电视、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一定程度控制的方式,是深刻而不懈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影响,通过媒介的去神秘化。
- 赫胥黎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教育。
避免让公共话语变成无稽之谈!